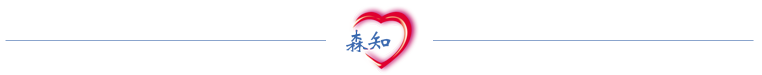从小活在对妈妈的恐惧之中
浏览量:5520 发表时间:2017-03-21
Diane Dweller从小活在对妈妈的恐惧之中。为了躲避妈妈的抽打,她会躲在床底,靠数床板和幻想熬过一天;在6岁时,她就希望妈妈死去。然而,在50年后,母女俩的关系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Diane甚至得到了来自妈妈的拥抱。
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?Diane如何进行自救?50年的时间,她明白了什么?今天,我们为大家导读Diane Dweller的自传《妈妈、躁狂与我(Mom, Mania & Me)》,介绍Diane与妈妈之间漫长的和解过程。本文中的“我”即为作者Diane本人。
小时候,我希望妈妈死去
从我有记忆开始,我就很怕妈妈。她会毫无理由地发脾气,对我大吼大叫,好像永远对我和姐姐感到不满。每次她发火,我就呆呆地站在旁边,手都不知道怎么放。
面对妈妈,我总感到自己弱小无力。我没有办法阻止她伤害我,也没法阻止她伤害其他人。有天下午我被姐姐的哭叫声吵醒,吓得我光着脚跑到客厅,发现妈妈正对着姐姐又打又骂。我希望自己能冲上前去拉住妈妈,我希望妈妈能快点死掉,这样姐姐就不会受苦了。那一刻羞耻感在我胸口燃烧。我并不是为了自己希望妈妈死而感到羞耻,我是为了自己无力保护姐姐而感到羞耻。
在我6岁那年,妈妈发生了意外流产。从那之后,她的脾气变得更加糟糕。只要我有一点让她不满意,她就会把我按在膝盖上,拿拖鞋狠狠抽打。每天早上睁开眼,我就开始恐慌:“妈妈今天会打我吗?” 我那时年纪小,没办法进行复杂的思考。但在妈妈日复一日的打骂下,我也被逼得想出一些“生存模式”:
首先,我会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,除了吃饭时不得不面对她之外,我都会躲在自己房间里。其次,在她提出各种匪夷所思的要求时,我学会了不去反驳,而是尽力去满足她的标准。有时我会想:“也许有天我做到她对我的期望,我就能得到她的爱了。”然而,即使我一次又一次地做到更好,她永远都能找到新的地方去挑剔我、批评我。
我不明白为什么她总是对我不满,我努力地找答案。后来我想起妈妈过去总说:“我想要一个男孩”。我忽然意识到:“是不是我是家里多余的女孩?是不是我从一出生、发出第一声啼哭开始,我就让妈妈失望了?”当时我很绝望,但因为年纪太小,即使对妈妈有怨恨,也不敢明面上进行反抗,只能用暗地捣乱来表示抗议。这种被动攻击一直持续到我的青春期。
青春期时,我对妈妈的感受很复杂
在我逐渐长大的过程中,我慢慢意识到“妈妈会打骂我,并不是我的错”。因为有时我虽然表现得无可挑剔,妈妈依然会发火。随着成长,我感到自己越来越有力,开始尝试正面地对抗她。结果,一次对抗导致了激烈的冲突。
1950年代,年轻女孩中流行穿牛仔裤上学。但妈妈不准我们穿,她认为“一个淑女就该穿裙子”。可我觉得自己长大了,有权力决定自己穿什么。于是我用攒的钱买了牛仔裤,在周五的早晨穿上,大摇大摆地走到餐桌旁面对妈妈。她看到我穿的裤子,嘴唇猛地绷紧、鼻孔因为怒气而一张一合。她对我大吼:“换掉!”我对她吼了回去:“我不换!”
像往常一样,妈妈抽了我一耳光结束了对话,我哭着跑回房间。过了会儿,妈妈走进房间,对着我问:“刚才阿姨看见了我打你,她有说什么吗?”直到这时,她依然不关心我的感受,只关心她在保姆面前的形象。
但是,从那次对抗以后,每周五我都会穿牛仔裤上学。妈妈默许了我的行为,但是每次看到我时,她都会作出不赞同的情态。每当这时,我就在心里默默地恨她。
但是,我对妈妈的感受是复杂的。除了恨,我也对她心存感激。在我10 来岁时,我被诊断出脊柱外突,需要去很远的地方做手术。当时只有妈妈能陪着我。后来每当我怨恨她时,我就会想起她在我手术期间对我的照顾,我认为她是在乎我的。
这让我感到很矛盾。一方面,我恨她,巴不得立刻离开她;但另一方面,她对我的好又令我困惑,我不禁想,是不是只要我做得再好一些,她就会更持续地爱我?即使我打定主意要逃离她,但我依然忍不住会渴望她的爱。
悲剧循环:为了逃离妈妈,
我进入了一段糟糕的婚姻
在高三那年,17岁的我遇到了25岁的Tony。我们一见钟情,度过了美好的三个月,期间Tony对我关怀备至,给了我从未有过的温暖。后来,Tony向我求了婚。他捧着我的脸,说会一直爱我。我一阵头晕目眩:我这样一个在妈妈眼中一无是处的人,竟然会有人爱我,竟然还想和我结婚?
一想到结婚后,我就有理由离开妈妈,和一个爱我的人组建家庭,我便兴奋不已。18岁的我不想继续上学,也不考虑将来的就业,只想逃离这个家,给我爱的人生孩子。婚礼后,我如愿搬离了家庭。然而不到一个星期,这段婚姻便出现问题:Tony开始不停地指责我、骂我没用。可每当我问他我哪里做错时,他又会说:“你应该自己明白。”
我绝望地意识到:原来我离开了妈妈,却又嫁给另一个“妈妈”。小时候的“生存模式”又启动了,我开始减少自己的存在感:每当他在家中,我就会呆在其他房间。此外,Tony毫无责任心,当我怀上第一个孩子、准备生产时,他依然在和朋友在另一个城市踢球玩,对我漠不关心。
人们可能很困惑,为什么一个男人如此糟糕,他的妻子还是不肯离开他?我想我知道答案,因为我被妈妈“训练”得太好了。常年来她都致力于让我觉得自己是个糟糕的人,不配得到别人的爱,要是我让别人不高兴了,那一定是我的错。Tony也总会说“我这样对你是因为你的错!”久而久之,我信以为真,认为他们虐待我真的是因为我不够好。而且,一旦离婚,我就又只能回到妈妈身边。两边都是火坑,我还能去哪儿呢?
这段婚姻持续了五年。五年来,我尽力维持,但最终我们还是选择了离婚。Tony从我们的住处搬了出去,留下我和我们的两个孩子。
妈妈一直不支持我离婚,在1960年代的美国,离婚是让家庭蒙羞的事。离婚后,我从妈妈那里获得的只有责怪与抱怨,没有一点安慰。她经常和我说,你丈夫会离开你肯定是因为你做错了事。每次她这样说,我都感到崩溃又不解,我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,让我的妈妈如此厌恶我。
转折点,有时只需要一件小事
离婚之后,我一边拉扯孩子,一边咬牙重拾我的学业。重回校园,我试着用学业重塑我的自尊,每一个好成绩、每一次成功的发言,都让我渐渐觉得自己也有值得骄傲的地方。而为了学业,我牺牲了和孩子的关系:由于压力大,当孩子让我烦躁时,我会下意识地打他们。有时我太着急了,就会对他们吼:“你们什么也做不好!”
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重复妈妈的恶劣行为,直到有天我整理小时候的房间,在抽屉底部翻出了一张叠起的、泛黄的笔记纸。纸张上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——
“当我长大,变成妈妈以后,我绝对不要:打我的孩子、对他们大喊大叫、骂他们搞砸了一切。“
我终于想起,这是我七岁的生日时写下的生日愿望。我这才明白,我彻彻底底地辜负了七岁时的自己,我成了像我妈妈那样的人。
从那时起,我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自我监控,一旦我发现自己有吼叫的前兆,我就提醒自己闭嘴、深呼吸,之后轻言细语地和孩子讲道理;当两个孩子发生纠纷时,我也先将他们分开,等他们都冷静下来后,再耐心地听他们解释,而不再像过去那样,不分青红皂白地责骂他们。我要让我的孩子们明白:“你们是可以信任妈妈的,妈妈是会认真倾听你们、重视你们的。”
同时,我也告诉自己,虽然妈妈对我造成的伤害已是既成事实,但我仍然能主动做些什么,来改善我现在和将来的生活。我发明了一个有用的仪式:每当我脑海中浮现出妈妈和Tony虐待我的画面,我就会拿出以前的照片,把它们撕成碎片,扔进马桶冲走。而每当我脑海中又响起妈妈恶毒的声音时,我会想象脑海中有一个录音带,通过拆掉这盒“妈妈录音”,我就像扔掉了妈妈对我的负面评价。
在自我治愈的过程中,我的新伴侣Rex也给了我极大的帮助。Rex爱我、尊重我。妈妈从来不会拥抱我和姐姐,但Rex却非常喜欢给我拥抱。和他在一起时,我第一次体会到了被爱的感觉。当妈妈在电话中批评我,我就在心中想着Rex满怀温情的脸,他给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持,让我应对母亲对我的伤害。
然而,即使我的婚姻生活变得幸福,我依然希望妈妈能爱我。对妈妈的爱的渴求,并不会因为得到他人的爱而消失。
我终于找到“对抗”母亲的方法
爸爸去世之后,我带着10岁的三女儿Shannon拜访了妈妈。妈妈打算和Shannon一起在厨房做蛋糕,而我在餐厅收拾桌子。一阵寂静后,忽然传来了妈妈恐慌的叫声:“不!不!不!你毁了我的蛋糕!哦我的天哪!你到底懂不懂切蛋糕!毁了!蛋糕全毁了!”
我急忙跑进厨房。Shannon显然吓坏了,她僵立在原地、下唇颤抖。看着我的女儿,我仿佛忽然又变回了小时候的我,面对妈妈的吼叫只能瑟瑟发抖。下一秒,我感到无比的愤怒:“她怎么敢伤害我的孩子?”我抱住Shannon,深呼吸,尽全力冷静地安慰Shannon:“蛋糕没有毁掉,Shannon。外婆应该在你切之前就仔细地告诉你切的方法,我会和外婆好好谈谈。”
在那个晚上,我翻来覆去无法入睡。我为妈妈的行为感到生气,也愤怒于自己为什么没有当场反抗她。我对自己发誓,我绝对不会让Shannon受到来自妈妈的伤害。
第二天早上,吃完早饭,我和妈妈一起上楼更衣。她看着我换上的衣服,讥讽说:“你该不会就打算穿这样出门吧?”我冷冷地瞪着她,愤怒在体内横冲直撞。我张开嘴,刻薄的言辞几乎要喷涌而出,但在内心深处,我忽然感到了一种深切的悲伤,像一盆冷水兜头浇下。我直直地看向母亲的眼睛,冷静而坚决地说:“这是你最后一次挑剔我。以后,我不希望听见你再批评我或者Shannon。”
我用一种超过了自己想象的沉着说:“我回到家里,是希望一家人能够团圆,能快快乐乐地在一起。而你对Shannon的吼叫、对我的挑剔,都让我们感到很不开心。如果你再这么做,我就会带着Shannon离开。”说完,我迅速地抱了抱她,转身下楼。
走在楼梯上,我膝盖发软、浑身颤抖。我忽然意识到,我终于做到了我渴望了四十多年的事:看着妈妈的眼睛,让她停止对我的批评。在那一刻,我感到自己真正意义上地长大了——我终于成功地赢了妈妈一次;同时我又感到了难过,因为我竟然需要在自己孩子遇到危机时,才能激发起足够的勇气去对抗她。
在那次谈话后,每当妈妈试图抱怨时,我都会看着她的眼睛,重复一句:“我们说好的。”虽然她看起来很不高兴,但是她确实闭上了嘴,而这就够了。这次成功的沟通给了我勇气和信心,并让我意识到了平静的力量:我不需要对着妈妈大吼大叫来实现我的目的,我可以成熟、冷静地表达我的需求。当我用成熟的方式和她沟通时,我也迫使她成熟地回应,而不是像个孩子一样一味地抱怨。
足够长时间以后,
我才愿意尝试释怀
随着妈妈逐渐老去,我对她的愤怒和恨意才逐渐消退。我慢慢地尝试去理解她,逐渐认识到妈妈同样受到自己过往经历的局限:她之所以不能对我和姐姐表达爱,是因为在她小时候,也没有人充满爱意地对待过她。既然妈妈不会表达爱意是因为她缺乏爱的经验,那么我可以给她作出示范,教她如何对他人表达爱意。——我可能早就知道这一点,但对她的愤怒让我不愿意这样做。
同时,我也愿意对自己承认,因为小时候她对我的虐待,我始终从负面的角度去评价她,选择性地忽略了她身上积极的一面:她是穷人家的小孩,在她成长的年代,人们认为女性只能“在家生孩子”;而妈妈超前地认识到,只有接受教育、参与工作,女性才能摆脱贫穷。最终她依靠个人奋斗,拥有了不错的收入。
于是,在有一次去看她的时候,我拥抱了她。她疑惑地问道:“你为什么抱我?”而我告诉她:“我就是想抱抱你呀”。后来,每次我要和她分别时,我都会拥抱她。这样的“仪式”持续了好几年。直到有一天,我又一次准备离开,92岁的妈妈忽然挣扎着想站起来。她说:“我想抱抱你。”那一刻十分短暂,在我的感受中却非常漫长,一瞬间我好像回溯了对母亲所有有过的感受,复杂的情绪全部得以释放,而终归平静。
如果让我对我的读者说什么,我最想说的是我得出了结论:我们能够一定程度上摆脱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,并且能不让它传递到孩子身上。与妈妈相反,我尽可能温柔地对待我的孩子。遗憾的是,因为从小感受不到来自家庭的温暖,我同样做不到频繁地对孩子表露爱意。
但是我很高兴地看到,当孩子们长大后,他们比我做得更好,我经常看见他们拥抱和亲吻我的孙子。家庭给我们的创伤,有时反而能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与指引,使得我们最终超越自己的父母,一代比一代过得更幸福。